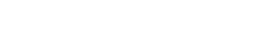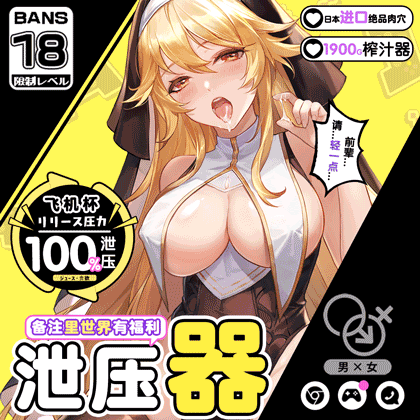关于直观的理解拉康三界,一个实在与符号的双向悖论:
拉乌尔( Raoul )与玛格丽特( Marguerite )是一对情人,他们打算在一个假面舞会上相遇;在那里,他们逃到一个隐蔽的角落,拥抱和抚摸对方。最后他们一起摘下面具,令人吃惊的是,拉乌尔发现他拥抱的是别的女人,不是玛格丽特,玛格丽特发现她拥抱的男人不是拉乌尔,而是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
那么我们清晰的看出来,这里的“现实”分为两个维度。第一个是事实维度,即是纯客观的,“实在的”维度。这可以代表着拉康的实在界。
另外一个则是双方幻想中的维度,臆想的维度,象征的维度,他们如何互相认出?比如说语言和感官,她看起来(像),她闻上去(像),嘴唇的触感(像)这一切都符号化为确定的信息——他/她就是我的伴侣。这可以代表符号/象征界,或者更清晰点,这是一场拟真,把它当作黑客帝国里面的场景吧,这整个场景都是数字拟真的。
请幻想一个新的结局,如果,他们结束后并没有摘下面具而是直接回家了呢?他们会发现今天其实不是和对方接吻吗?
如果实在从头到尾都没有显现(实在的定义就是如此),那么通向实在的唯一途径就只有符号和象征。
而吊诡的是,这种对于实在的体验决定于未来的选择。选择摘下面具(直面实在界)和不摘下面具(选择象征)会共时性的改变过去——你决定,你过去是在亲吻爱人还是陌生人。
当然,实际情况下实在并不会以其本身显现而是通过符号化,象征化,弗洛伊德所谓移情,投射等等机制转化成语言,从而浮现于意识,被符号捕获,下面是齐泽克对于上述问题的阐释:
在经历征兆时,我们恰恰是在“造就过去”——我们恰恰是在制造符号性现实(symbolicreality),即发生于过去的、早已遗忘的创伤性事件(traumaticevents)的符号性现实。
因此,我们不禁在科幻小说的“时间悖论”中,看到了符号过程的基本结构(elementary structure of thesymbolicprocess)中出现的幻觉性的“实在界的幽灵”(apparition in the Real),即所谓内在的、在里面翻转过来的8字型:一种循环运动,即一个陷阱,我们在那里只能如此前行——我们在移情中“越过”自己,然后在某个我们早已到过的地方看到了自己。
这个悖论之所以是悖论,是因为,这个多余的迂回,这个追加的陷阱(supplementarysnare)——即“越过”自己(“走进未来”),以及对时间方向的逆转(“走入过去”),不只是对发生在所谓现实中的客观过程的主观幻觉或感觉(现实与这些幻觉无关)。那个追加的陷阱,反而是所谓“客观”过程得以成立的内在条件,是所谓“客观”过程的内在构成因素。只有通过这样的额外的迂回,过去,即事物的“客观”状态,才能回溯性地呈现为它总是呈现出来的样子(what it always was)。因此,移情是一种幻觉,但关键在于,我们不能绕开它,直奔真理:真理本身是通过移情特有的幻觉构成的——“真理源自误认”(拉康语)。
关于精神分析的工作:
实在界在被语言拖拽到象征层面时所拉起的视觉场域,而这里的语言同样是无意识/或是梦境的等价物,它们拥有相同的结构(这也是拉康最著名的观点之一),精神分析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实在的语言解码并整合:
因此精神分析被视为符号化(symbolization),即对无意义的想象性踪迹(imaginarytraces)所作的符号性整合(symbolicintegration)。这一观念暗示我们,无意识的主要特征是想象:无意识是由“无法融入主体历史的符号性发展(symbolic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’shistory)的想象性固着(imaginaryfixations)”组成的。结果,无意识“是将在符号界(theSymbolic)中现身之物,或说得更确切些,多亏在精神分析中取得的符号性进展(symbolicprogress),无意识是将要成为的某种事物(something which will have been)”。
关于一个笑话或标准的精神分析疗程:
有一个著名的黑格尔式的笑话,完美地展示了真理是如何源自误认的,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是如何与真理本身相契合的。在20世纪之初,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坐在同一列火车上,面面相觑。
波兰人紧张地晃动着身子,一直盯着犹太人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激怒了他,最后,他再也抑制不住地破口而出:“告诉我,你们犹太人是怎样成功地从人们身上榨取了最后一个硬币,使自己腰缠万贯的?”犹太人回答说:“好吧,我告诉你,但不能分文不取,你先付我5个兹罗提(波兰币)。”收到钱后,犹太人开始讲了:“首先,你拿一条死鱼,割下它的头来,将其内脏装在一杯水中。然后,大约午夜时分,月圆之时,你一定要把这个杯子埋进墓地……”“那么,”波兰人贪婪地打断了他,“如果照你说的做,我会成为有钱人吗?”“不要操之过急,”犹太人回答说,“这不是你要做的全部;如果你想听下去,你必须再付5个兹罗提。”再次收下钱后,犹太人继续讲他的故事。不久,他又伸手要钱,没完没了。最后波兰人怒不可遏了:“你这个肮脏的无赖,你真的认为我没有注意到你想干什么?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,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!”犹太人平静而温顺地回答他说:“好吧,现在你已经明白,我们这些犹太人是如何……”
在齐泽克的视角下,这个笑话成为了一场精神分析治疗的范式。
首先一开始,波兰人便陷入到移情关系中——对他而言,犹太人即是欲望的保管者,是知情的大他者,因此波兰人不断将希望与努力施加其上,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回报。而犹太人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象征/符号场域的视差,一片神秘模糊之地。
犹太人用模糊的意义,实际在符号体系之外的事情继续他的移情欺诈。
而终于当波兰人醒悟,出离愤怒的时候,他已经喊出了真相: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,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!
在醒悟的同时他走出了移情,明白了自己只是空耗精力。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精神分析的治疗师对他耳语:“他并没有骗你,他的确让你明白了犹太人是如何骗钱的。”
这样便彻底的击碎了幻象,让波兰人明白了实质——自己只是学到了该学到的东西。
而只要这东西成为了实在之物,它也就是失去了可以作为想象而承载移情的功能,于是移情便彻底消失了,幻象也得到了清算。
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2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2楼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3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3楼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4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4楼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5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30 5楼









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40 16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40 16楼
 CFBDSIR2149-1943 2022-8-40 18楼
CFBDSIR2149-1943 2022-8-40 18楼